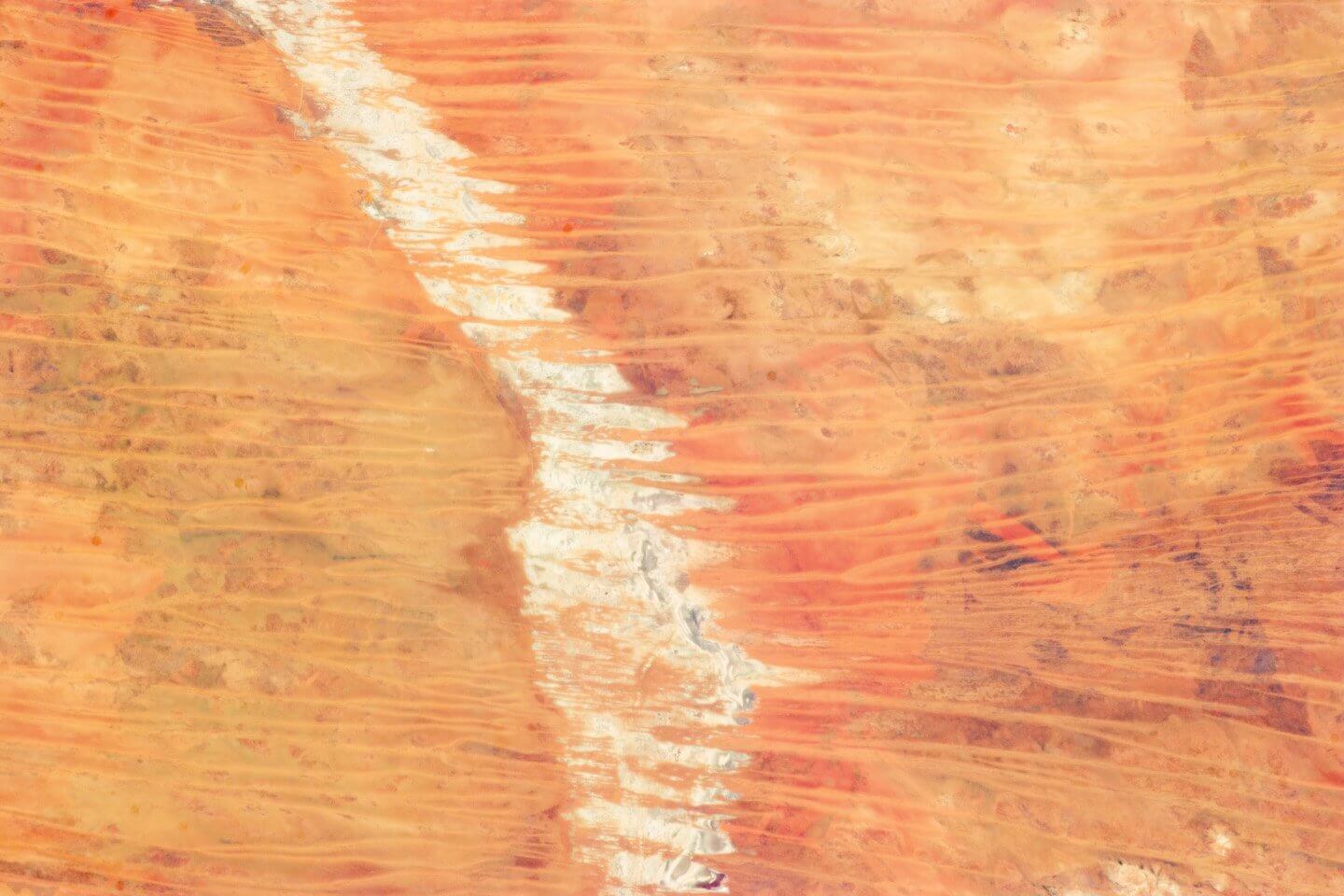type
status
date
slug
summary
tags
category
icon
password
summary
01.
老北京的胡同,香椿树莹莹绕绕的从斑驳的墙面上附着过去,在那面泥灰抱不过砖块的土墙前做了一排绿莹莹的修饰,在上面展开个地摊似的,得用指头尖拨开层叠肥厚的兀自在风中颤巍巍的叶子,才能看到幕后的真实,倒也是成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取景地。无人看管的溜达猫照旧不惊不慌,慢悠悠踏着闲散的步子走过,脚上四簇蓬松的白毛衬托着它总像是乌云罩雪,剩下一对着了画家笔上调和的亮蓝色的猫眼石一般无二的眼睛,在一片赤黑的体态里闪闪烁烁。
附近还在念大学的小姑娘,时不时刻意绕过一条街来探望它,细长的手指里捏着一根撕开小口的猫条,凑到近前来,清脆的喉音亲昵地唤它的名字,是清脆脆几声二大爷——附近率先获得命名权的胡同大妈们随口定下的信号,很默契的音调在半空里约略俏皮的拖出个长音,有总是透出些害羞的不好意思的劲儿,仿佛总是不怎么很确信,总归对着过于乡土气的名字感到陌生,即便是来来回回念叨出口,也仍感到诧异,不那么确信一样。
然而毕竟叫了其他的名字,猫也是不认的,学德文的小伙曾出个主意,逗趣着喊它莎士比亚,只有人能听懂其中打趣做笑意味的东西,猫哪里认得?到底还是讪讪然的作罢,照旧唤它一叠声的二大爷,不多时,猫咪就慢悠悠荡到眼前来,白生生四只脚着地的动物,一黑墨炭似的黑,浮动在地面上,望见的不太真切,是一片的乌云压着游动过来,从天际上落下来一样,黑的和白的都那么纯粹,不掺杂一星半点的污秽。有时候姑娘们小声说像踩着四只拨了壳的嫩山竹,那样白的四只脚爪,看了几次都觉得难以置信。怎么,要说是流浪猫,干净成这幅样子,谁又敢说是没人照顾的?
女学生们唧唧嚓嚓,每次乱哄哄嬉笑逗骂起来,也不在意周围人好奇的看过来的眼光,看就看!新世纪的子民,怕什么。活着么,就要活一个痛快,何必躲闪别人的目光,说到底心虚的可又不是她们呢。就这样你推我搡跟猫逗趣一阵,猫吃得饱了偶尔也肯躺下来懒洋洋恩赐地翻开它的肚皮,这是混得娴熟了,才能荣幸地得此恩典,然而毕竟也是少有,多半的时候仍是一抬尾巴,颇为傲慢的转身就走,脚爪踏在胡同口的青石砖面上,悄然无声的,一跃又一跃,不知怎么就沿着墙缝上了屋顶,转瞬消失得踪迹全无。猫么,多半是这样闲散的个性,逼迫不得,陈俊南深韵此道,在这之前偶尔他还能得到机会紧跑两步,把这猫囫囵地兜进怀里,管它是情愿还是不情愿,硬是带到水管下面洗刷干净。说是焕然一新也不为过吧,女学生的揣测大抵没错,这猫算是不亲近他,但毕竟没有他那么足智多谋。
陈俊南这个人邪乎的很,好端端的,谁会跟一只无人看管的流浪猫计较这么多!然而自从他上次出了胡同一不留神没注意脚下,不小心踩着了猫尾巴,只听见乌云盖顶的猫惊跳起来,尖利刺耳的长嚎让那么一个优雅的生物硬是成了飞鸿踏雪,眼神幽怨地往后一撩,从此无论陈俊南如何呼喊,从二大爷喊到二祖宗,从二祖宗叫回二大妈,也浑然不应,彻底不肯在他面前露面了。
一只猫故意躲着你走,你还有撞见它的份儿么?陈俊南只是苦笑,心里也不大服气,那么高的个子,漂亮洒脱的身量往门口一站,连着三天要摸清楚这二大爷“下班”的门道。它躲着他,总不能也躲着女同学吧?就这么堵着气追了三天又三天,最后还是只得认命,道一句跟猫不熟,恐怕上辈子是冤家对头。心里面也有股气儿,合着暑热的调,不肯轻易褪下,感觉这个夏天还没开头就颇为不顺,再迷信一点,他都要为今后的种种不幸找个苗头。得罪了猫二爷,那还有个说法?然而毕竟这事对错参半吧,他自己没留神,猫难道还看不见么,那么鬼灵精的一个,居然肯呆在原地傻等着疼那一下?他倒是能原谅自己走神。
幸亏人猫殊途,不然把这话讲出去,猫更不肯凑他近前了。
不过话说回来,虽然陈俊南是丧失了替二大爷净身的权利,二大爷却也没见有多脏污,还是那副吃得油光可鉴的晶亮皮毛,在暮色里一块游动的墨迹,像有谁在背后用毛笔的毫尖在它身上点了一点。那么精妙干净的笔法,颇有中国山水的意境,竟是个从宣纸的收笔运势里冒出来的猫,叫人忍不住为它喝个好彩。陈俊南用眼梢打量一眼,心里就明白了个七七八,好小子,他心里面好笑着,嘴巴跟着吊起来,难怪你对小爷爱答不理的,这是背后有着管事的主子呢。
这在他概念里存在的“管事主子”却毕竟没有头面,他蹲在胡同头随性地想东想西,女学生么,常来是常来,但要说清闲到给流浪猫洗澡,却还没能做到这一步。该说不说,怎么逼着一个不爱水的猫老老实实洗干净,还不泼你一身水来报应的?饶是绝顶聪明的陈俊南也没辙的事!想到家里面那几件经年洗不净的衣服,沾着挂着随处可见的猫毛,也不敢扔进洗衣机里,怕猫毛成了飞絮,牵挂连累了别的衣服。要说是胡同口的土皇帝各路大妈们么,大妈们又实在不好说,但是横竖琢磨了到底比学生可靠,时间又多,平日看管自家的孩子都能各展风采,对付一只小畜生,应当是不在话下。然而陈俊南心里还是犯嘀咕,总觉得哪边都不太站,到最后那无头无脸的形象罩上一层细细的纱网,像个等待撩开盖头的花嫁新娘子,影影绰绰的,目光里看不真切,旁观的人心里面总是膈膈应应,犹如隔着窗户纸瞧隔壁家的电视机,撩拨的心里发痒,人天生对于未知的向往!
后来嚜,也终于是知道了的,揭开猫主子这层叠的春纱水,到底是望见了湖底下的面貌。
夏日将过未过的时候最为讨厌,空气里总是沉浮着燥热的氛围,人心惶惶的颇不宁静,这股无处派遣的闷热的劲儿,时而在一场寒雨过后得到片刻的纾解,那感觉像是一贴清凉的薄荷药膏敷在烫伤的皮肤上,透着丝丝难得爽快的安宁。然而不过多时挥之不去的暑热就再度大驾光临,好一个怎么赶也不肯走的姨太太,偏要往门口一站,分明清楚这院子里终于是要没有她的位置了,就是有不那么肯乐意走得痛快,左顾右盼流连忘返的恋恋不舍,半只脚斜斜踏在门边框上,不肯梗着身子大方方跨出去,闹得在场的人里没有脸色好看的,给宾客看着,也只是徒增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。
陈俊南倒是不苦夏,他在怎么倒反天罡的气候里都自诩能岿然不动,脾气好、胃口好、样貌品相更是上行的门道,照旧该打趣的打趣,该扯皮的扯皮,一句话能换来他兑水喝半斤的老北京片儿汤。他跟人聊天,天南海北的胡侃乱吹,到最后从室友到同学见着他就一个头嗡鸣成两个大,恨不能掉头绕开走。凡他所过之地,皆如大风过境,除他以外声息全无,路过的无比噤若寒蝉,屏息凝神,怕的是一个眼神对上了就被抓去胡侃,这事儿全凭一个运气。
到后来系里面都流传开了一句话,躲得过初一,躲得过十五,躲不过陈俊南这一劫难。心里面念一句阿弥陀佛,头脸一股脑往下塞进领口里,一个个显出副愁云满面行色匆匆的面貌,别着脸,拧着个儿,贴墙跟蹭过去。
抓人要抓倒霉的,终归还是让陈俊南逮着一个,倒霉蛋长得和倒霉蛋这三个字倒是毫无关系,白生生照着宣纸着色的衬衫,浆洗得过分干净了,映在人黑漆漆的眼睛,反倒觉得心口惶惶然的难受,像一口气别在了喉咙眼,就那么心不甘情不愿的,上不来也下不去地吊着,怕的是把那身清白突兀地给毁了。额前的短发切分的细细碎碎,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想到老堂口快要濒临失传的特色龙须酥,金灿灿黄酥酥头发丝,那样精细的缠连起来,凑近一闻,满面的飘香,足以把人的七魂六魄都吸附了大半个。只是那发丝修饰的太过利落,干净的薄削,是艺术家手中一柄雕刻刀的锋芒,又黑得太深太重,约略的沉甸甸的,落在前额和脑后,不太像是真的。
墨黑的发根下面,到竖起的衣领口中间一段,出露一截脖颈。皮肤有些白,放在北方的气候里,使人无端就想起冬天的霜花冷。说是白,倒也不是瓷器的质地,经过窑子里文火慢火,才得以哄出来的一块易碎的工艺品。碰不得又动不了的,他那种白,总显得黯淡,别别扭扭,透着冷意的调子,和那写意画里腾出来的衣服一比,就更显得暗哑,有点水淋淋的意思,不明显也不惹眼,只有把目光刻意地往他露出袖腕的皮肤上放,才能琢磨着揣摩出这份不够透彻的白来。修身的长裤一刷的黑色帘幕垂落到脚踝,不清楚是不是故意留出的一段悬空着晃荡,在鞋面的上方偶尔曳动几下,不像一般的青年,注意力从不肯放在外貌上就蒙混过去,一截裤脚软趴趴塌在鞋子上,总是不够爽快,而且又避开了高腰的袜子,就堂皇的显出他的脚踝,又是不讨人厌的留白,打眼看过去不觉得好笑,反而无端填了几份让人望而生又不动声色的凉气。
个子也不短,即便是不认真地扫过去,也能意识到这是个高挑的形象,就是下颌骨太锐,眼梢还太长,一字的刘海飘忽落下来,又是一个乌云盖顶,阴影倾斜着拢住这张脸,饶是平日也多加几笔蓄势待发的攻击性质。
但陈俊南是何许人也?别人绕开走的,他偏要凑上去,和他这个行为模式同理,他就爱惹那些事非短长,也没别的心思,就图一时新鲜给自己平添那么些从麻烦里蹦出来的乐子。
他余光一瞥见就清楚这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,你就看他那眼睛的角度,看人都是懒洋洋慢悠悠从上往下兜过去,好一个天然嘲讽的视角。他偏不信邪,小臂带着大臂,胳膊往上一拧,抡起来画出个风火轮,风火抡画到半截就在人家肩头上收了关。他一胳膊没打招呼就勾在人家的脖颈上,闹得对方身子没什么防备地蓦然僵了僵,手里端着的马克杯狐疑地从水平角度倾斜了一个角,猫的眼睛一般无二的瞳孔酝酿着心思就猛调过头来,被一网兜打捞进网子里的倒霉鬼倒真像个鬼。那张面庞转过来,让陈俊南一颗心不确定地紧绷,好似八音盒拧上太多圈的弦,此刻砰砰砰忙碌的转不过来,吱呀呀牙齿反酸的声响。后来他自己想起最开始的这回事,意识到这是名为懊悔的东西在拉响他直觉的警报,可惜他自由自在惯了,早就把后悔这种意识扔开到九霄云片外。
什么意思。
声音也像猫的动静,琉璃灯盏在眼前晃一晃,嗓音里的寒气塞了薄荷叶,隐藏一个个锐利的荆棘刺。一丛丛倒钩抖开了,统统都在这里漫不经心等着他。陈俊南第一次发现原来话语还真是长着眼睛的,短短四个字翕张出四只眼睛一瞬不瞬紧逼着他,让他多话的嘴忽然成了一口干涸的古井,心里急忙得发慌,越是慌就越是没个曲谱,是唱念做打的一套词难听的走了调,磨盘压下来沉的驴子走不动道,在原地直打拐子。他倏忽觉得自己那条胳膊压着的不是人家的肩膀,反而是他的命门。有点讶异的悲哀一路从脚底窜上来,人还真是分了三六九等、七七四十九,只能是硬着头皮让肚子里的半吊子油瓶打起晃,话没出来先在嘴里空弹一个音,哟字拉的老长,像是把他前半生的好日子都唱个完了,徒然添进一丝痛切的感伤。
还能有什么意思,看见新来的小爷我就走不动道儿,您丫转系的还是跨院的啊?
他故意把话音调高了说,颇有种给自己拔高个挑衅的含义,受到了攻击和冒犯后急于亮出自己的爪子,像极了圈地,在这里证明自己的不好惹。然而对面一双眼睛冷飕飕把他的话都冻掉了,黏在窗户上的红剪纸让霜花一抹,水珠陡然滴落下来打湿边角,红纸阴湿了半边后自觉没趣的往下滑,他这是为了置气,说完了却又有点不确定的反悔,自己先觉得没劲,忍不住又矮了几分。
他这才发现对面远不是什么乌云盖顶的猫儿样的形象,那样安安静静的一个,塑在他身边,一尊不易摇撼的坚实的大理石雕像,上面还有着云石的纹路,格外天然的牢固,真品和赝品的区别!所以么,明知道转系跨院背后都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门路,谁也不愿让人这么直接的问了,背后能有什么退路?是交了钱还是请了饭抑或是四通八达的罗马城里的家眷,一句话出来让人尴尬的支支吾吾,哪儿像是这位爷,那只眼睛,还真是——那样一双眼睛!
陈俊南看了看猛然抽回了胳膊,再往前凑凑又终于不太好意思,脚趾尖尴尬地在地上划出一个吓着了的半圈,倒是比他自来熟的风火抡好看得多,一片嘴唇嗫嚅着又不知如何是好。哪里吃过这种亏,他这样牛哄哄的人物?
到底是不确定那只眼睛有什么问题没有,阳光闪闪的,眼珠也一般无二闪闪地看过来,难怪他觉得像猫,可猫哪里长成了这样。叫人又惧又怕又忍不住感慨句美丽非常。一整个宇宙的摇撼,承装进一只人的眼瞳里,何等可怕!
他这边没等到一句回答,就遥遥听见喊来一句夏老师——往前左拐,来开个会。这位收起目光就像合上一把扇子,望过来和撤回去都一样干脆,不给人留什么余地。他径自转回身走开,神色照旧是淡然无声的,走了之后也不再有经过的痕迹。只有陈俊南在原地发愣,总觉得自己是撞见了一个活鬼。
大夏天的,他在墙根连着打三个冷颤,忽地后悔非常。
- 作者:二手蓝烟
- 链接:https://www.bluess.store/article/15184fd0-387c-80af-a426-ec8a58b8ee12
- 声明:本文采用 CC BY-NC-SA 4.0 许可协议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